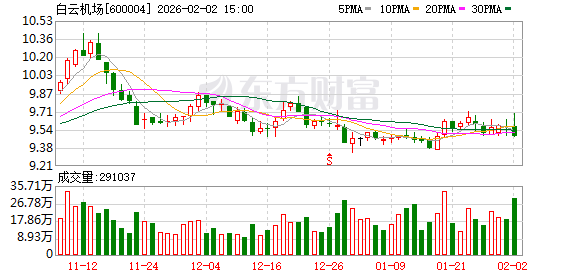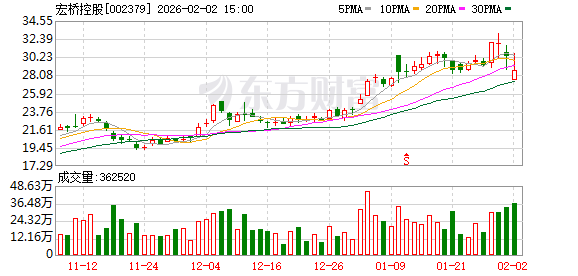乡野蔓草,难斩是情根
我的故乡,是地图上一个需要放大数倍才能瞥见轮廓的小点,那里的人,一生都被两条线牵着:一条是脚下泥土的颜色,春绿秋黄,不容更改;另一条是祠堂族谱上的名字,昭穆有序,不容僭越,情感?那是藏在庄稼收成、婚丧嫁娶背后的暗流,是深夜炕头上几句含糊的叹息,是村口老槐树下,几个模糊身影掠过时,旁人迅速交换又立刻垂下的眼神。
村东头的阿香嫂,是这暗流里一个醒目的漩涡,她是外乡嫁来的,带着一股子我们村里女人没有的水灵与不安分,丈夫长年在外务工,她一个人操持田地,照顾老小,腰杆挺得比田里的高粱还直,她的利落与鲜活,像一块石子投入村里这潭沉静了太久的水,起初是涟漪——男人们帮她挑水打谷时的过分殷勤,女人们聚在一起纳鞋底时,对她衣着的挑剔与模仿,后来,涟漪下起了暗涌,关于她和村西那个同样独自带娃的退伍兵“大山”的闲话,渐渐像夏天的蚊蚋,嗡嗡地,驱之不散。
他们其实没什么“实据”,不过是有人看见大雨天,大山扛着铁锹帮她疏通堵了的垄沟;不过是农忙时,两家的打谷机偶尔并在一处轰鸣;不过是她家小子总爱往大山家跑,喊“山伯”喊得比亲爹还亲,但在这密不透风的村庄里,“不同”本身就是罪证,他们的坦然来往,在旁人眼里成了欲盖弥彰的暧昧,那暧昧,在闲人的舌尖上被反复咀嚼,加工,渐渐有了眉目,有了细节,成了夜里刺激又道德的谈资。
直到那年秋收,阿香嫂的婆婆,一个干瘦如核桃的老太太,在晒谷场当众摔了阿香嫂递上的水碗,瓷片炸裂的脆响,割破了午后的沉闷,老太太没指名道姓,只对着空气咒骂“家宅不宁”、“狐狸精勾魂”,那毒蛇似的目光却死死缠着不远处正扛麻袋的大山,阿香嫂的脸,先是血红色,继而褪成惨白,最后是一种死灰,她没哭没闹,弯腰,一片一片去捡那些碎瓷,手指被割破了,血珠滴在金黄的谷粒上,触目惊心,大山青筋暴起,拳头攥了又松,转身走了,背影像一座移动的、压抑的火山。
那以后,河上的木板桥似乎更朽了,村东到村西的路,仿佛被无形的墙堵死,阿香嫂更瘦了,眼神里的光熄了,成了真正的“嫂子”,符合一切规训的沉默妇人,大山则变得愈发暴躁,常对自家孩子无缘无故发火,然后蹲在门槛上,望着远方出神,一蹲就是半天。
我曾以为这就是结局,一场乡村闲话与陈旧规训的必然胜利,直到去年春节回村,听闻大山急病,是阿香嫂不顾一切,深夜敲开赤脚医生的门,又守着直到他城里的亲戚赶来,流言再次短暂复活,却意外地没掀起太大风浪,或许是人情在生死面前,显出了它应有的重量;或许是岁月流驶,让看客们也感到了疲倦。
我离开那日,特意绕路从村外田埂走过,残雪未消,覆盖着僵硬的土地,就在那田垄的背阴处,在一片萧索的枯黄与灰白之间,我竟看见一星极淡的、胆怯的绿——不知名的野草,从冻土与碎石缝里探出了一点头,它那么弱,那么不合时宜,一场倒春寒或许就能要了它的命,可它就在那里,固执地绿着。
我忽然了悟,乡村的“乱情”,或许从来不是道德册页上简单的污点,它是被严格秩序挤压下,人性本能曲折的求生;是孤独灵魂在漫漫长夜里,试图彼此照见的微光;是那些未曾被文明词汇妥善安放的依赖、怜惜与懂得,它生于贫瘠的土壤,长于压顶的舆论,注定扭曲,难堪,甚至带着破坏性,如同石缝里的草,形态未必优美,但那挣扎着向上的生命力本身,却透着一种凄然的真实。
风又起了,带着熟悉的尘土味,我回头望,村庄在暮色里静默如坟,那些爱恨、挣扎与叹息,终将被时间这座最广袤的田野深深掩埋,了无痕迹,只有人性深处那点星火不灭的渴望,大约会像野草,一茬一茬,在每一个春天,试探着,破土而出,这无关对错,这只是活着,在厚重的黄土之下,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