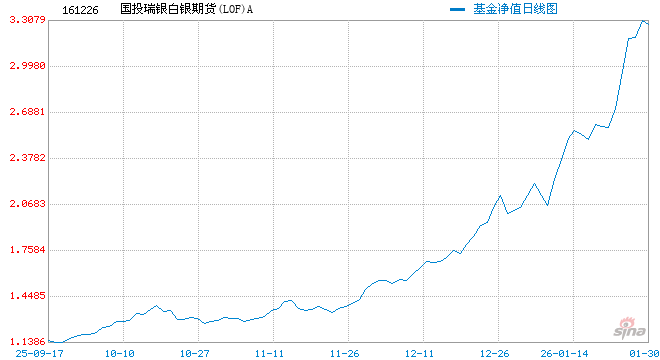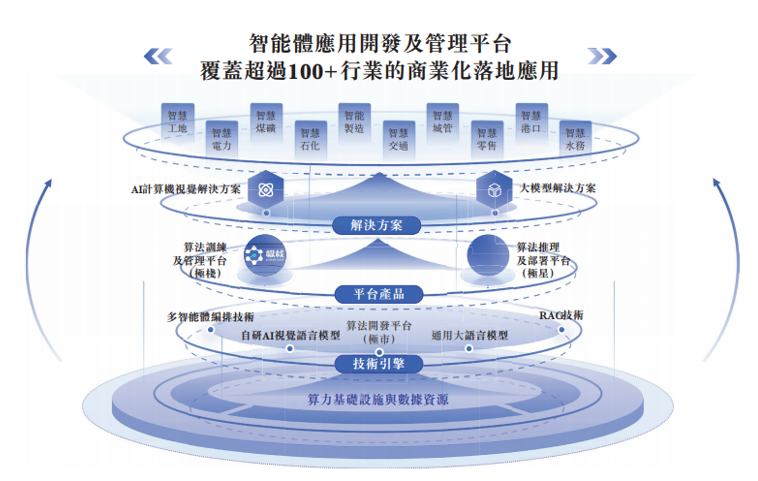中国人其实好色,但好得高级
最近几年,生活美学成了一个热词,人们谈论侘寂风、极简主义、莫兰迪色系,仿佛高级感必须与低饱和度、无彩色挂钩,家里的墙要刷成“高级灰”,衣柜里黑白灰驼成了安全牌,连手机壁纸都偏爱清冷的太空或深海的意象,我们的视觉,似乎正在经历一场集体的“色盲化”训练,将鲜亮、饱满、对比强烈的色彩,悄悄归为“俗气”与“过时”。
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被长期误解的词:好色,在中文的日常语境里,它略带贬义,指向一种肤浅的欲望,若我们拆开来看——“好”,是喜爱、懂得、追求;“色”,是色彩、是视觉呈现的万千世界。“好色”的本真,应当是一种对色彩敏锐的感知力、热烈的欣赏力与富有创造力的运用能力,从这个意义上说,传统的中国人,骨子里其实是“好色”的,而且好得极为高级,好出了一整套宇宙观、哲学观与生活美学。
我们的“好色”,藏在文明的基因里,它不像西方绘画传统中基于科学的光影与固有色,而是源于对自然最诗意的观察与归纳,古人从天地万象中提取出“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”五色,将其与“五行”(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)、五方、五时甚至五脏相对应,色彩从来不是孤立的视觉刺激,它是一个庞大文化符号系统的有机部分,朱红不仅是红,它是太阳、是火、是血液、是生命与庄严;青色不仅是蓝或绿,它是春天、是东方、是木的生机、是“天青色等烟雨”中那份纯净的期待,这种色彩观是象征的、哲学的,甚至是道德的。
这份高级的“好色”,在传统艺术与器物上绽放得淋漓尽致,看故宫的琉璃瓦,是那样沉静又耀眼的明黄,那是中央戊己土的尊贵,是皇权的天象化表达,移步江南园林,粉墙黛瓦,点缀着碧绿的芭蕉、火红的枫叶、金黄的银杏,色彩在有限的空间里随四季流转,如同一幅活的“浅绛山水”,古代的织锦与瓷器,更是将色彩的运用推向极致,一件明清的云锦或缂丝,可以同时运用十几种色线,织出金碧辉煌、繁而不乱的图案;一个宋代的钧窑瓷碗,“入窑一色,出窑万彩”,那抹浑然天成的“雨过天青”或绚烂的“窑变”紫红,是人力与天意合作的色彩奇迹,那份含蓄中的绚烂,内敛下的奔放,是后世任何高饱和色块都无法比拟的意境。
中国画虽以水墨为宗,但绝非无色,大师们的“浅绛”或“青绿”,用色极尽精妙,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石青、石绿层层渲染,辉煌壮丽,那是青春视角下对山河最炽热的礼赞,更不用说敦煌壁画,历经千年,那些取自矿物与植物的朱砂、石绿、青金石蓝,依然在幽暗的洞窟中散发着撼人心魄的瑰丽光芒,讲述着佛国世界的绚烂想象,这里的色彩,是信仰,是叙事,是超越现实的精神图景。
从何时起,我们对色彩变得如此“谨慎”甚至“恐惧”了呢?这种审美的转向是复杂的,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、西方现代主义设计思潮(强调形式与功能,色彩常作为辅助)的传入、以及快节奏都市生活催生的对“宁静”、“简约”的心理需求,共同促成了我们对高纯度、高对比色彩的疏离,我们害怕“出错”,害怕显得“不够有品位”,于是纷纷躲进中性色的安全区,色彩,这个原本最直接、最富有情感张力的视觉语言,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大幅降调,变得规训而乏味。
我们失去的,或许不仅仅是一抹亮色,而是一种与生命本源相连的活力与勇气,色彩是情绪最直接的载体,心理学研究早已证实,不同的色彩能显著影响人的心理与生理状态,热烈的红激发能量,宁静的蓝舒缓神经,充满生机的绿缓解疲劳,当我们长期将自己包裹在灰调之中,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压抑自身情感的多样性与表达的欲望,古人“伤春悲秋”,对季节色彩的变迁有着细腻的感怀,而我们穿梭在钢筋玻璃的灰色丛林里,对自然的色彩轮转,似乎只剩下手机日历上冰冷的节气名称。
真正的“好色”,不是庸俗的堆砌,而是懂得在恰当的语境中,让色彩说话,它可以是苏州博物馆那一方粉墙前,由光与影精心裁出的一株倔强石榴的红;可以是妈妈手织的旧毛衣上,那种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的、温暖又扎实的枣红色;也可以是菜市场里,西红柿、茄子、青椒、玉米毫无心机地堆叠在一起,所迸发出的那种活色生香的、治愈人心的视觉盛宴。
重拾“好色”的能力,是重拾一种认真生活的态度,它意味着我们愿意睁开眼睛,真正去“看见”:看见春天第一抹柳芽的嫩黄,看见夏日黄昏天际的粉紫,看见爱人衣裙上一抹特别的蓝,看见自己厨房里碗碟搭配出的小小愉悦,我们可以从一小步开始:为书房添一个明黄色的靠垫,在餐桌上换一套草木染的靛蓝餐巾,甚至,只是认真地为今天的午餐搭配一道色彩明亮的菜肴。
最高级的“好色”,最终是通向内心的丰富与自在,它知道“水墨无色,胜有色”的空灵境界,也同样欣赏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的烂漫生机,它不排斥莫兰迪的温柔雅致,但也不畏惧马蒂斯式的狂野热烈,它理解色彩背后的文化密码,更珍视色彩带给当下生活的即时欢愉。
愿我们都能勇敢地“好色”起来,不再被所谓的“高级感”绑架,而是信任自己的眼睛与感受,在生活的画布上,调配出独属于自己生命的、鲜亮而不刺眼、丰富而不杂乱的那一份色彩,毕竟,一个真正懂得欣赏“色”的世界的人,其内心世界,也必定是层次丰富、充满生机的,这或许,才是我们从古老智慧中,所能继承的最活泼、最愉悦的生活哲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