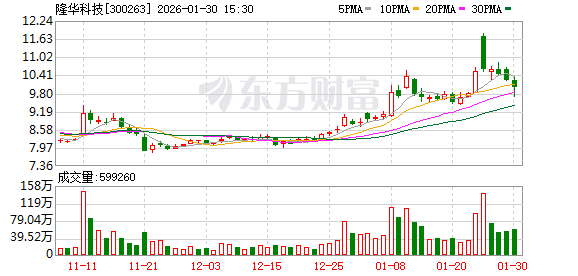越危险越迷人,为什么我们都向往娇艳人生?
深夜十一点,路过那家总是很晚打烊的花店,暖黄灯光下,老板娘正在整理新到的朱顶红,饱满的花苞,鲜红欲滴,在墨绿叶片的衬托下,有种惊心动魄的美。“这花真娇艳。”我忍不住赞叹,老板娘抬起头,笑了:“是啊,娇艳,可你知道吗?朱顶红的鳞茎有毒,误食会恶心呕吐,甚至心跳紊乱。”她擦掉手上的泥土,“最美的东西,往往也最危险。”
这话像一枚小石子,投进心里,漾开一圈圈涟漪,我们似乎总是如此——既渴望“娇艳”带来的感官冲击与生命力的明证,又本能地畏惧那绚丽背后可能隐藏的刺、毒,与莫测的代价。
“娇艳”这个词,本身就站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上,一边是“娇”——易折的、脆弱的、需要被呵护的;一边是“艳”——浓烈的、夺目的、极具侵略性的,它描述的状态,是竭尽全力地绽放,是把所有生命力浓缩在当下,孤注一掷地呈现美,这种美,因其极致,而显得短暂且不安,像《红楼梦》中的晴雯,“心比天高,身为下贱”,她的美貌与伶俐何其娇艳,可那锋芒,那“撕扇子作千金一笑”的任性,终究为她招致风雨,命运如同骤雨下的海棠,我们被那份不驯的、鲜活的生命力吸引,又为它显而易见的脆弱而揪心。
植物学提供了一个更冷酷也更具诗意的视角,在自然界,许多最娇艳的花朵,恰恰是最“危险”的,除了朱顶红,还有夹竹桃、曼陀罗、虞美人……它们用最绚烂的色彩和形态吸引传粉者,同时又用毒素武装自己,警告天敌,这是一种生存的悖论与智慧:极致的吸引力,是繁衍的策略,也是危险的宣言,这份“危险”,不是单纯的缺陷,而成了它魅力的一部分,是它区别于平庸之美的身份标识,人类的审美,在潜意识里,是否也读懂了这种来自生命底层的、危险而诱人的信号?
放眼我们的文化场域,“娇艳人生”的意象,同样与“危险”如影随形,玛丽莲·梦露的金发、红唇与裙摆飞扬的瞬间,定义了半个世纪的好莱坞娇艳,聚光灯下那具被无数目光消费的躯体,与她私人世界里的不安、依赖与最终陨落,构成了传记中最令人心碎的注脚,作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,如葛薇龙、白流苏,哪一个不是在时代的倾轧下,用尽心思将自己的人生经营得“娇艳”一些?那是一种在逼仄环境中开出的花,带着精打细算的虚荣与孤注一掷的悲凉,美则美矣,却总透着苍凉的手势和宿命的底色。
我们向往“娇艳人生”,究竟在向往什么?或许,是在向往一种“高浓度”的活法,在秩序化、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,生活常常被稀释成重复的片段,而“娇艳”,意味着情感的浓烈、体验的峰值、存在的显著性,它是对平庸的反叛,是向世界宣告“我曾如此炽热地活过”,哪怕它伴随着不稳定、更高的情感损耗(如极致的喜悦也意味着更深的失落),甚至社会风险(如打破常规带来的非议),人们依然前赴后继,就像明知焰火短暂,我们仍愿仰头,等待那照亮夜空的一瞬华彩。
纯粹的、无拘束的“娇艳”近乎奢望,更多的“娇艳人生”,是在“娇”与“艳”、“安全”与“危险”之间,走一条小心翼翼的钢丝,是职场女性精心勾勒的红唇与得体干练的西装之间的平衡;是创业者押上全部热情与身家时,仍努力维持的理性规划;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精心修饰的生活片段时,内心对真实与虚构界限的那份清醒,这是一种成年人的“娇艳”,懂得绽放,也懂得为自己负责。
回到那个花店深夜的意象,娇艳的朱顶红,需要适宜的光照、水分,园丁需知晓其毒性,小心处理,最理想的人生状态,或许并非一味追求毫无阴翳的绚烂,而是成为自己生命的园丁——懂得培育内心那株独特的花卉,让它有机会绽放出最本真的色彩;同时清醒地认识自己的“毒性”与边界,不伤及他人,也避免被自身的烈性反噬,在安全区与冒险区之间,找到属于自己节奏的“绽放区间”。
我们或许会明白,令人向往的从来不是毫无代价的完美,而是那种知情后仍选择盛放的勇气,是了解生命脆弱本质后依然投入的炽热,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,那带着刺的娇艳,才是生命最诚实、也最动人的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