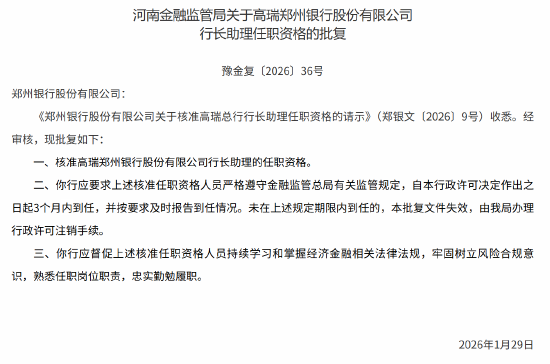桃色年华的消亡史
老家的院子里,那棵歪脖子桃树终于还是被砍掉了,电话里,母亲轻描淡写地说,虫子蛀空了,一个雷雨天,自己就倒了半边,留着也危险,挂了电话,我却觉得心里某块地方,也跟着“轰隆”一声,塌陷了下去,那塌陷处露出的,不是什么深刻的悲伤,倒像是一捧被时光烘得干透、一触即碎的桃木屑,带着一丝若有若无、快要遗忘的甜腥气。
那甜腥气,是我整个童年盛夏的底色,桃子的“桃色”,首先是一种蛮横的嗅觉与触觉,不是超市里那些规整光鲜、气味淡薄的果子,老家毛桃的香,是劈头盖脸的,你还没走近院子,那股子熟透了的、近乎发酵的甜腻就混在热风里撞过来,像一只热情过度、汗津津的手,等到真捧在手里,茸毛扎着掌心,痒酥酥的,指甲掐破薄皮的瞬间,“刺啦”一声轻响,汁水迸溅,那香气才达到了顶点——一种混合了阳光、泥土、树叶汁液,以及果实自身魂魄的、复杂而生动的气味,我们等不得洗净,在衣襟上胡乱蹭两下毛,就急吼吼地咬下去,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,黏黏的,招来三两只不知疲倦的蝇,那种吃相,是顾不得体面的,是动物般的、全然的沉浸,汁水划过嘴角,流到脖颈,最后那桃核,总是被吮吸得泛白,没了半点滋味,才依依不舍地扔掉,指尖上,那股甜腥气能顽固地停留大半天,任你用井水搓洗多少次,凑近了闻,总还有一缕影子,那是一种烙印。
后来,“桃色”变成了视觉,变成了晚霞,变成了同桌女生突然飞上脸颊、又迅速褪去的红晕,那是十几岁的年纪,世界开始罩上一层柔光滤镜,开始注意到,桃花不是一团团模糊的粉雾,它有五片精巧的瓣,蕊心一点深红,娇弱地颤着,开始读懂诗词里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悸动,开始为一些无端的忧愁沉默,那时以为的“桃色年华”,是天边永不坠落的火烧云,是一场盛大序曲的开端,所有的未来都像枝头的花苞,鼓胀着,充满无限可能,我们谈论理想,用幼稚而真诚的笔触描绘远方,深信那份心底泛起的、朦胧美好的情愫,会如同桃树一般,自然生长,开花结果,那时的“桃色”,是预告,是憧憬,是一张尚未填写、但似乎注定华美的邀请函。
再后来,“桃色”成了形容词,却与桃子、与晚霞、与脸红都渐渐失了关联,它出现在闪烁的网页边角,出现在暧昧不清的流言标题里,成为某种隐秘、香艳、甚至略带贬义的事件的代称,这个词被从枝头摘下,扔进了大众文化的染缸,迅速地被欲望化、符号化、消费化,它不再需要经过漫长的生长、等待阳光雨露、积累甜分,它成了一种廉价的、即时可得的感官刺激,一抹被用滥了的、挑逗的色调,我们消费着“桃色新闻”,如同消费一罐流水线上生产的、糖精过量的桃子味汽水,只有刺激的甜,没有回味的核,更没有指尖那股洗不掉的、真实的生命气息,那个原本承载着自然丰饶与青春心跳的词语,变得轻薄、油腻,甚至有些不堪。
院子里的桃树倒了,我试图在城市的超市里,寻找一个能唤醒记忆的桃子,它们被泡在保鲜剂里,个体匀称,色泽完美,像橱窗里的塑料模特,我买下一颗,洗净,郑重地咬下,果肉是清脆的,汁水是充足的,甚至甜度也是经过科学测算的、最宜人的标准甜,可是,没有那劈头盖脸的香气,没有黏腻滴淌的狼狈,没有茸毛扎手的触感,更没有那股贯穿始终的、生动的甜腥气,它很好,但它不是“桃”,它只是名叫做“桃”的另一种水果,我平静地吃完,将光洁的核丢进垃圾桶,洗了手,手上什么也没留下。
我终于明白,我失去的,不仅仅是一棵树,或是一种水果的“本味”,我失去的,是一整套感知世界的方式,那种需要等待、经历毛躁、容忍瑕疵、最后在狼狈的享用中获得极致慰藉的体验;那种将情感与自然物候紧密相连、赋予其厚重隐喻的思维;那种“桃色”能同时代表果实之味、霞光之美与少年之羞的、浑然天成的语言体系,它们都被更高效、更规整、更直白、也更单薄的东西取代了,我们获得了清晰的四季如春,却失去了咀嚼四季的牙齿与脾胃。
我的桃色年华,或许早在我不曾察觉的某个时刻,就已经随着最后一滴黏稠的汁水,滴落在故乡干涸的泥土里,迅速蒸发了,如今萦绕心头的,只是它被烘干后,那一点点碎屑的幻影与回响,而当我试图向更年轻的一代描述何为“桃之夭夭”,何为“投我以木桃”时,我竟有些语塞,因为在他们可能关联的词典里,“桃色”的第一释义,或许已与我珍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个夏天,毫无关系了。
那是一种静悄悄的消亡,没有告别式,如同那棵桃树的倒下,只存在于母亲电话里一句平静的交代,而我,是这个消亡时代里,一个携带着无用记忆的,最后的遗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