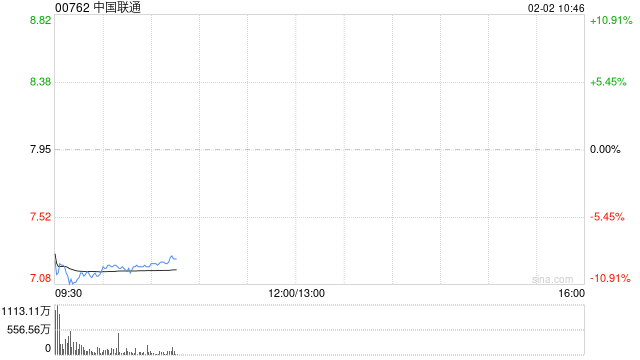阿宾列传,一个普通人的失败史诗
朋友们,今天我们不谈风口,不聊变现,来讲一个“失败者”的故事。
他叫阿宾,我的高中同学,也是我们那届学生里最“没出息”的一个,当同学们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讨论KPI和OKR时,阿宾守着他父亲传下来的那间老式照相馆,在县城东街的梧桐树下,一守就是十五年。
照相馆叫“时光定格”,名字和他的人一样,带着点不合时宜的浪漫,橱窗里永远摆着九十年代风格的艺术照,背景是粗劣的手绘布景——埃菲尔铁塔、椰林树影,玻璃门上贴着的“数码冲洗”、“证件快照”红字,边角已经卷起,在这个手机像素以亿计算、美颜滤镜一秒换脸的时代,阿宾的营生,堪称数字洪流里一座安静的孤岛。
他的“失败”是有据可查的,同学聚会,他是永远的“背景板”,有人融资千万,有人海外定居,话题落到阿宾身上,总是一阵短暂的沉默,然后是礼貌的、略带怜悯的寒暄:“阿宾现在挺好,安稳。”安稳,成了对一事无成最体面的注解,连当年成绩倒数的“胖辉”,都靠着做微商在省会买了两套房,开上了宝马,只有阿宾,他的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,收入、见识、人脉,一切都停留在毕业那年。
我曾以为,阿宾是麻木的,是接受了这种温吞的、毫无波澜的命运,直到那个下午。
我去找他冲洗一些老照片,店里没有顾客,他正埋头擦拭一台老旧的海鸥双反相机,神情专注得像在修复文物,我们聊起近况,我不可避免地抱怨内卷、焦虑、中年危机,阿宾听着,很少插话,只是偶尔点头,他站起身,从里间抱出几本厚重的相册。
“你看,”他翻开一本,塑料膜哗哗作响,“这是五金店的老陈,每年孙子生日都来拍一张,拍了十二年,从小娃娃拍到初中生,他说,在我这拍的,有‘人味儿’。”
又翻一页:“这是街尾的柳奶奶,老伴走了十年了,她每隔几个月,就拿着同一张结婚照来,让我帮着修一修折痕,或者重新过塑,她说,别的店嫌她事多,只有我从不嫌烦。”
相册一页页翻过,是无数张平凡的脸:新生儿、新婚夫妻、金婚的老人、毕业的学生、穿着不合身西装第一次去面试的青年……阿宾记得他们很多人的名字,记得一些拍摄时的趣事,他的照相馆,没有网红打卡,没有爆款流量,却忠实而沉默地收集着这座小城普通人的生命刻度。
“我技术可能不是最好的,设备也是最老的。”阿宾合上相册,笑了笑,笑容里有种清澈的坦然,“但我知道,张阿姨希望把她眼里的皱纹修得淡一点,却又不能全没;李叔想把他下岗前得的奖状拍进全家福里,他们买的不是一张照片,是一份心安,是一点体面,是觉得自己的那一刻,值得被这样郑重对待。”
我忽然哑口无言,我们这些所谓的“成功者”,在数据的浪潮里拼命奔跑,追逐一个个宏大的目标、光鲜的标签,却常常在深夜里感到虚无,困惑于自身存在的意义,而阿宾,他锚定在飞速流逝的时间之河中央,用最笨拙的方式,为那些同样被时代大叙述忽略的个体,保存着微不足道却独一无二的生命证据,他从未离开,于是成了所有人的“故乡”。
他的相机很慢,一张照片需要耐心,他的盈利很薄,勉强维持生计,他的世界很小,方圆不过几条街巷,他没有改变世界,甚至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,但,在“时光定格”昏黄的灯光下,在化学药水微弱的气味里,他让许多匆匆而过的人生,有了沉甸甸的、可触摸的重量。
离开时,夕阳给老街镀上金边,阿宾站在店门口对我挥手,身后橱窗里的假埃菲尔铁塔闪闪发光,那一刻我明白,我们所沉迷的“进步”与“成功”,或许只是庞大社会机器规定的单一赛道,而像阿宾这样,在主流叙事之外,找到自己的位置,并以恒久的温度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联结,何尝不是一种更坚韧、更有人情味的“成功”?
在这个崇尚速度、放大声量、追求裂变的时代,阿宾的“失败”生涯,像一颗温润的卵石,静静地躺在河床底部,提醒着我们:或许,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被多少人看见,而在于你如何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人;不在于你跑得多快多远,而在于你是否为那些需要“定格”的瞬间,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支点。
阿宾的故事,是一部写给所有“慢一拍”的人的列传,它不励志,但足够温暖;不激昂,但充满力量,这力量来自坚守本身,来自在浮华世相中,认领并照亮自己那一方微小而确定的星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