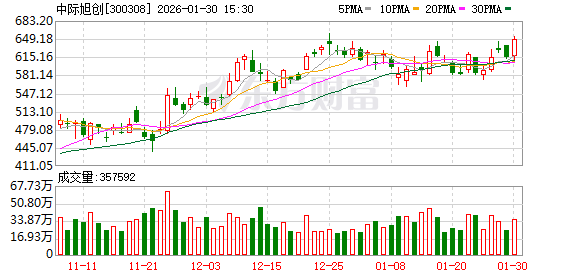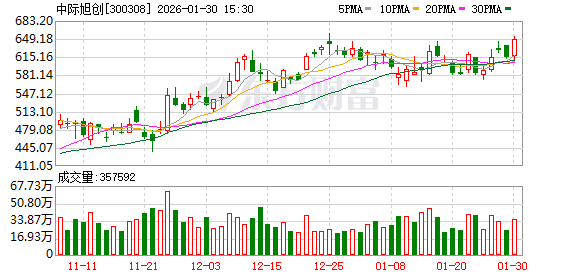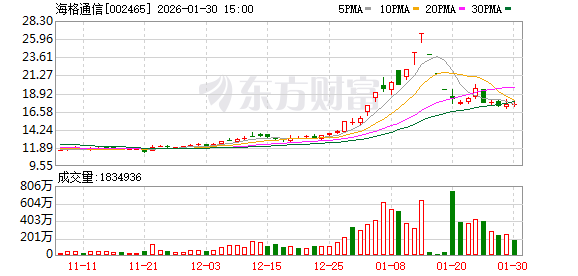永不重播的夏日剧集
那座南方小城,夏天是被溽热浸透的,空气稠得化不开,像一块巨大的、半透明的琥珀,将整条街道的人和物都凝在里面,阳光白晃晃地砸在柏油路上,蒸腾起一片摇曳的蜃景,街角那棵老榕树是唯一的例外,它撑开一团沉甸甸的、墨绿的荫凉,像个与世无争的君王,蝉声是这片领地的背景音,从早到晚,不知疲倦地织着一张密不透风的声网,听得久了,人也会恍惚,仿佛时间被这单调而固执的鸣叫拉长、黏住,不再向前。
老榕树对面,是一家永远半掩着门的自行车铺,铺面小且旧,墙上挂满黑乎乎、辨不出模样的工具,地上散落着轮胎、链条、螺丝帽,空气里常年混杂着机油、铁锈和橡胶的气味,铺子的主人,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,终日在昏暗的光线里敲敲打打,而阿宾,是这片灰色背景里,一抹突兀又鲜活的亮色。
他是老头的孙子,那年大概十五六岁,皮肤被夏日烘烤成均匀的小麦色,汗水在他光着的脊背上淌出一道道发亮的溪流,他很少穿完整的汗衫,总是一件洗得发白、肩头开了线的背心,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,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,不是在帮着祖父卸轮胎、紧辐条,就是在门口的荫凉地里,鼓捣一些我们看不懂的玩意儿——用废弃的链条和齿轮组装一个只会空转的“永动机”,或者把几块磁铁和铜线圈缠在一起,试图让一枚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。
我们都叫他“阿宾”,带着一点亲昵,也带着一点对他那些“古怪”行为的、善意的嘲弄,他不怎么跟我们这群在街上追逐打闹的野孩子混在一起,但也不驱赶我们,有时我们玩弹珠滚进了他的铺子,他会用脚尖精准地给我们拨出来;有时我们的“战车”(自行车)出了毛病,扭扭捏捏地推过去,他瞥一眼,也不多话,蹲下来三两下弄好,摆摆手,意思是“快走,别挡路”,他的手很脏,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油污,但那双手又异常灵巧,那些在我们眼里复杂如迷宫的机械问题,在他手下总是迎刃而解,他像是这条街的“街头物理学家”,用一种粗糙而直接的方式,掌管着所有轮子的转动。
我真正与他有“交集”,是在一个同样闷热的午后,我的“坐骑”——一辆父亲淘汰下来的二八杠“凤凰”,在一次鲁莽的冲锋后,链条彻底罢工,像条死蛇般垂下来,伙伴们呼啸而去,我沮丧地推着这堆沉重的废铁,挪到了榕树荫下,对着自行车铺张望。
阿宾正坐在一只倒扣的铁皮桶上,低头看着一本卷了边的书,看得入神,连有苍蝇在他肩膀上起落都没察觉,我喊了他两声,他才如梦初醒般抬起头,他没有立刻看我的车,目光先在我脸上停了一秒,又落回手里的书页,然后迅速合上,塞到一堆旧轮胎后面。
“链子卡死了,”他走过来,蹲下,只说了这么一句,他没有用工具,就那么用手,用力掰扯着那根油腻腻的链条,手臂和脖颈的肌肉绷出清晰的线条,汗水大颗地滴落在滚烫的地面上,瞬间就消失了,弄了好一会儿,链条才“咔嗒”一声复位,他站起身,在裤子上擦了擦手,从墙边一个破脸盆里撩起一点水,冲了冲手上的油污。
“好了。”他说。
我连忙道谢,掏出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,他摇摇头,没接,眼神却飘向那堆旧轮胎,他犹豫了一下,走过去把刚才那本书抽出来,拍了拍灰,递到我面前。
“看过这个么?”
那是一本《基督山伯爵》,封面已经破损,用牛皮纸仔细地包了书皮,我摇头,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,除了课本和《少年文艺》,我们几乎接触不到别的书。
“拿去看吧。”他把书塞给我,语气不容拒绝,“别弄脏,别弄丢,看完了……再跟我说说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,从一个同龄人手中接过如此“厚重”的东西,我带着一种神圣感,把那本书藏在了书包最里层,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,我的心分成了两半:一半仍在烈日下的街道上疯跑,另一半却跟着爱德蒙·邓蒂斯,沉入了伊夫堡阴森的地牢,又在波光粼粼的地中海上,燃起复仇的火焰,书中那个宏大、遥远、充满激情与阴谋的世界,与眼前黏稠缓慢的夏日现实,形成了奇异的对冲,我仿佛透过一个秘密的孔洞,窥见了另一种人生的磅礴与狰狞。
再去还书时,我对阿宾的感觉完全不同了,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满手油污、沉默寡言的修车少年,而是一个秘密的持有者,一个领路人,我们的话依然不多,但默契地建立了一个“借阅-归还-讨论”的隐秘通道,通过他,我又陆续读到了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苔丝》,甚至一本残缺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,书页间有他留下的、歪歪扭扭的铅笔划痕,有时是一句没头没尾的感想,有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,我们的讨论也仅限于情节的惊叹,或对某个人物的简单好恶,更深的东西,我们那时都还说不出来,只觉得心里被一些陌生的、汹涌的情绪涨满了。
又一个夏日的尾声,一场罕见的台风袭来,狂风像一头巨兽,在街道上横冲直撞,撕扯着一切,雨不是下,而是成片地泼洒下来,所有人都躲回了家里,第二天风停雨住,满目疮痍,老榕树被折断了一根巨大的枝桠,惨白的新茬触目惊心,我蹚着积水走过街道,看见阿宾和他祖父正在铺子里收拾,满地狼藉。
他看见我,从一堆湿漉漉的杂物里,捡起一个东西,那是他用来听广播和音乐的一个旧收音机,外壳裂了,天线也歪了,他捧着它,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是用手指,慢慢抹去上面的泥水,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他擦拭的不是一台收音机,而是某个我们共同珍视的、却已被风雨打碎的时光。
再后来,我去了外地念书,寒暑假回来,自行车铺还在,老头更佝偻了,但阿宾不常在了,听说他去了城里的机械厂做学徒,后来又有人说他跟人去了南边,那条街渐渐变了模样,老榕树被市政移走,铺上了整齐的花砖,自行车铺最终关张,原址开了一家灯火通明的便利店。
我再也没见过阿宾,那些在榕树荫下,混杂着机油味、蝉鸣与纸张气息的漫长夏日,那些关于遥远世界的最初震颤,都被封存在了记忆的琥珀里,有时我会想,阿宾后来去了哪里?他是否还在鼓捣他的“永动机”?他是否还记得那个借书还书的沉默伙伴?
成年后,我读过更多更艰深的书,走过更多更繁华的街,但那个南方小城的夏日,那个满手油污却递给我一本《基督山伯爵》的少年,始终是我精神世界里一个独特的坐标,他并非什么启蒙大师,我们之间也没有深刻的灵魂交流,但他像一扇偶然推开的窗,让我瞥见了闷热现实之外,还有辽阔的风在吹拂,他的形象,最终和那棵老榕树、那间昏暗的铺子、那些被汗水与机油浸透的午后,熔铸在了一起,成为一种象征——象征着我们每个人都曾拥有过的、那个懵懂而炽烈的探寻年代,那种探寻无关功利,甚至没有明确方向,它仅仅源于一种本能的好奇,一种渴望突破自身环境限定的、朴素的生命力。
阿宾的往事,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散落在天南地北的、共同的往事,它们没有精致的剧本,没有预设的结局,像野地里自由生长的植物,带着粗粝的生机,最终沉寂于时代的巨大轰鸣之中,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个树荫,那个铺子,那个可以为一本破书心潮澎湃的下午,但我知道,有些东西并没有消失,就像阿宾当年试图用磁铁和线圈点亮的那盏小灯,光芒或许微弱,却真切地亮过,那光芒,曾照亮过一个少年望向远方的、最初的瞳孔。